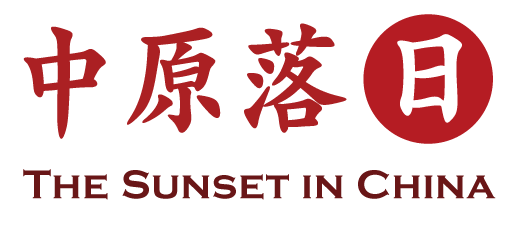
第五章
這是黃玫到家的第二天上午。
家裡人都因事出去了。只有黃玫一個人坐在房間發呆。房內雖然佈置得花花綠綠,但因是出自黃丁氏和丁維庸之手,不免有些庸俗之氣。
窗外的陽光射進房內,看著房中那些考究的設備,是從前沒有的。因此在她的心中充滿了驚疑與不安,尤其是東廂房內和床上供人吸大煙的那些器具,以及大門外邊牆上掛的那塊榮記土膏行的金字招牌,更讓她有一種說不出的厭惡和憎恨。
她反覆思索家中發財的原因,她怕聽到母親絮叨的話語,她也怕見僕役們恭維諂媚的面孔。只是想知道錢的來源,家裡如何致富?是不義之財嗎?
可是她想了又想,我如同一隻雛巢的小鳥,流浪快兩年了。媽是多麼想念我啊?她老人家看見我回來,歡喜得流下眼淚,我不能辜負她的慈母心….。
黃玫正在凝神細想,東廂房的門一開,女僕陳嫂輕聲地走進房,笑著說:
「小姐!水已經放好了,請你去洗澡吧。」
「怎麼走,現在就去嗎,我換件衣服。」
「不用了,小姐,我都給你準備好了,我帶你去。」
陳嫂笑嘻嘻地撩起門帘,示意讓她先走。
她打開了自己的手袋,正在整理衣服時,突然間聞到一股濃烈的異香。只見牆邊堆著幾疊牛皮紙包,都是尚未啟封的鴉片大煙土。她不忍看,也不願看,趕忙把自己的提包收好,跟隨陳嫂出了房門,沿著客廳後的走廊到了後院。
這所後院本來是很荒蕪的,自從黃家鴉片生意興隆,大發利市,黃丁氏和丁維庸僱來花匠重新整理,轉眼間變成一座幽雅清靜的小花園了。黃玫不禁停下腳步,瀏覽園中的景色,但見百花爭艷,修竹成蔭,與往日大不相同。
她轉了個彎,看見從前與方明在一起讀書下棋的小書房,已經改造成一間設備齊全的小浴室了。
陳嫂走到浴室門口推開兩扇門扉,裡面靠左有一排長方形格扇,格子裡有兩扇活動小門,門的正中縣掛一面全身鏡,鏡下就是一架大白磁浴缸,缸內盛著大半盆冒熱氣的溫水。
「小姐!」陳嫂笑著說:「你洗吧,我替你擦背,好不好?」
「不要了。陳嫂,你不要走,替我守住外面的門,不能讓任何人進來。」
「就是啦,小姐。你放心的洗吧,不要滑倒哦。」
陳嫂說了這句話後,立刻把外面的一道門關上並加上鎖扣,站在門外替她把門。她便大聲向裡邊說:
「小姐!你聽到我的聲音吧,我已經鎖好外門了,你就不必擔心啦,快洗快洗,別涼了水。」
黃玫聽了陳嫂的話,自己又把房門一鐵鉤掛上,不由對鏡端詳,對自己看來也有幾分羨愛了。再細看自己的小腹,雖未出現胎形,已有結實的一塊東西在內。正在幻想,這時陳嫂在外面喊道:
「快洗吧!小姐,水冷了是會感冒的。」
黃玫聽了連忙回神。
「陳嫂!我問你。」黃玫一面洗一面問:「你知道嗎?我媽到那裡去了?」
「哦!你問老太太呀?」陳嫂放大音量說:「她是坐車子到花牌樓唯新服裝店去了。她怕驚動小姐,臨走時就關照我替你放水,要你洗澡換衣服,她一會就回來的。」
「你知道我媽她是出去做什麼嗎?」黃玫凝神聽。
「小姐!」陳嫂坐在外面笑著說:「你真是那一輩子修來的福呀!太太說你要回來,在十天前就把屠先生選給你的料子,送到花牌樓一家成衣店,她說她已為你做了七八件的新旗袍新洋裝,準備你回來穿的呀。太太出去就是去拿你的新衣服呀!唏唏唏!」
「真的嗎?陳嫂?」黃玫感到十分訝異。
「當然是真的。」陳嫂嘮叨的說:「你還沒看見那些料子有多好看呢,花花綠綠,大紅小紫的,什麼顏色都有,聽說都是東洋上等的好料子。」
「別說了。」黃玫蹙著雙眉,很不耐煩地問:「陳嫂,你剛才說什麼屠先生,是什麼人哪?」
「唷!屠先生你不知道啊?」
「不知道,一點也不知道。」黃玫詫異茫然。
「哎喲!小姐,你不知道屠先生啊?」
「不知道。」黃玫如墜霧中。
「屠先生就是屠隊長嘛,在南京是很有名的!」
「屠隊長,他很有名?」黃玫更加迷茫了。
「對啦。是屠隊長。」
「他是什麼人?」
「什麼人,我也搞不清,小劉說,他是什麼什麼東洋人手下的隊長吧?」
「東洋人!」黃玫感到不解說:「你!你說什麼?」
「咦….?奇怪呀,怎麼小姐你不認識屠隊長啊?」
「不認識,一點也不認識。」黃玫不耐煩地說:
「我離家很久了。你快說清楚,他怎麼會跟我家扯上關係的?」
「這,我可不太清楚,我到這裡,還不到三個月。反正你也別問,依我看,你們現在的家業,與屠隊長有密切關連的。」
黃玫聽到這裡,忍不住心中的氣惱。一面穿衣一面向室外問:
「陳嫂!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?別再吞吞吐吐的,對我說清楚,好不好?」
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,我真的不太明白。不過,我聽說那位屠隊長常唸著你的名字。」
「唸著我的名字?」黃玫驚異。
「不但唸著你,還常常指著你說話呢。」
「指著我說話?」黃玫推開格扇門,邊穿衣服說:
「我才回家,他怎能指到我呢?」
「哎育!小姐不是的呀。」陳嫂撲嗤地一笑說:「我是說他常常來,指著東廂房牆壁上掛著你的那張大相片!」陳嫂說了摀住嘴笑。
「我的大相片?」黃玫又感到驚異。
「是的。聽說你的那張大相片的金框,還是屠隊長出的錢,叫庸爺到太平路一家大玻璃店配的呢。真好看!小姐你真是美麗,難怪屠隊長這樣的喜愛你呀。」
「一一」黃玫面有怒色。
「小姐,你幹嘛不高興啊?」
「陳嫂我問你。」黃玫臉色嚴肅的說:「你一定要對我說實話,不然我會生氣的。」
「小姐,你說,只要我知道的,我一定會全告訴你,請你相信我。」
「我媽怎麼會認識這個姓屠的?他為什麼要在我的身上打歪主意?」
「這我可不太清楚啊。只是有一次在廚房裡,我聽小劉和朱司務在閒扯….。」
「扯什麼?」
「你昨天回來,太太她沒把這件事對你說呀?」
「我媽見我回來歡喜得不得了,一切的事,等我睡足了有精神再說。所以,我什麼都不知道啊。陳嫂!全都說給我聽,一點也不要保留,好不好?」
陳嫂像是很神秘的樣子,向門外四下探看,轉臉向黃玫笑著說:
「大約是在去年的什麼時候,聽說那時這裡還在賣零燈,什麼人都能來這裡抽幾口。有一天,這位屠隊長也來這裡嚐試零燈的滋味,抽著抽著,可就被他發現啦!」
「發現什麼?」黃玫問得很急。
「就是我剛才說的,牆上掛的那面小姐你的大相片,他看見小姐長得美麗,他就動心啦。當時!」
「當時怎麼樣?」黃玫神情緊張。
陳嫂咳嗽一聲,嚥了一口涎沫說:
「當時太太和庸爺,在生意上需要屠隊長幫忙,就把你許配給他了。」
「一一」黃玫臉色蒼白,未說一句話。
她氣得一時不知說什麼話。接著陳嫂又說:「聽說庸爺和太太為了發展生意,還用了屠隊長不少的錢呢!」
「陳嫂!你對我說的話,句句都是實話?你沒有騙我吧?」
「哎唷!小姐」陳嫂急得臉紅脖子粗的說:「我家在六合鄉下,是信觀音菩薩的,我敢賭咒,我要是騙小姐會遭五雷劈頂,會不得好!!」
「好啦好啦。」黃玫舉手一揚說:「陳嫂,你別再說啦,我相信你就是了。」
「當然是真的。」陳媽很得意地說:「屠隊長有錢有勢,人也不老,我看小姐你將來一定會享福的呀。」
「好了,陳嫂。」黃玫淡淡的說:「別再說了,我相信你的話,我們到前面去吧。」
陳嫂聽了黃玫的話點點頭,二人才進門檻,不料正和迎面走進客廳的黃丁氏撞個滿懷。陳嫂看見笑著對黃玫說:
「呀!小姐,老太太回來了,你看她手中抱的都是你的新衣服呢!」陳嫂說了又向丁氏笑著說:
「老太太,小姐問過你好幾次了,你怎麼現在才回來呀?」
「我不是對你說過嗎?」黃丁氏把懷中的衣物,放在沙發椅子上說:「我要替你小姐辦的事都辦了沒有?」
「我都照著太太說的,我已侍候小姐洗澡。」
黃玫看見媽媽,沒說什麼話,丁氏卻笑瞇瞇的迎上前去說:
「小玫呀!我臨走關照陳嫂,要她侍候你洗澡換衣,她做了沒有?」
「洗過了。」黃玫聲音不悅地說:「你幹嘛要為我費心?我又不是三歲小孩子。」
「乖乖!不是的。」丁氏滿臉笑容,邊走邊說:「自從你離家後,兩年來,媽對你日思暮想,好孩子,從今以後你就在家別離開媽。來!聽媽的話,把這幾件新衣穿上試試看,合不合身?」
「不,我不穿。」黃玫說:「這一年多來,我在外面什麼都不講究了。穿上新衣就感到很蹩扭,你放在那邊吧。」
「好孩子!」丁氏柔聲細氣地笑著說:「在家可不比在外呀,在外穿得隨便一點沒人恥笑。在家可不能哪。你若不穿好看的衣服,就是家裡的下人也會笑你的。況且!我們的家不比從前了。聽媽的話嘛,你先來試試這一件,合不合身?」
丁氏邊說邊解開那個布包袱,取出其中一件藕荷色錦繡鳳朵花短袖旗袍,把它抖開,送到黃玫的面前笑著說:
「快來穿上,媽要看看你的新模樣。」
「媽!你就別再勞神了。」黃玫正色的說:「你快點把這些衣服全收起來吧。說實話我很討厭這些東西!」
「討厭?」丁氏感到訝異不解地問:「孩子,你洗澡受涼了吧?」
「我沒有受涼,是有些頭暈,我!去睡一會。」
黃玫說完,雙眉緊鎖,走到丁氏的大床前,就倒在床上睡著了。
丁氏看見女兒一臉的不高興,很小心地拉過床上一條鴨絨被,慢慢把被蓋在她身上,輕輕的說:
「乖孩子!我知道,你昨天折騰一夜未睡好,你就多睡一會吧,睡醒了起來吃飯。」
丁氏見黃玫未說什麼,又用手輕輕掠掠她的頭髮,看她睡著,才躡手躡腳地走出房門,不禁自言自語的說:
「噯!這孩子的脾氣,還是和從前一樣,一點不如意就不說話。唉!難得菩薩保佑,她已經平安的回來了。」
太陽西下,黃家大門邊停下一輛寬形的大馬車。
黃家的雜工小劉從車上跳下來,幫助馬車伕,將簇新的彈簧銅床抬下來。他把銅床放下快步進門到客廳,高聲喊道:
「老太太!銅床買來了。你看好不好?」
「多少錢?」丁氏漫不經心撩開門帘問。
「我不知道,是庸爺買的。又寬又大,他叫我僱車送回家。」
「庸爺他怎麼不回來?又瘋到那兒去啦?」
「他在路上碰見趙二同一夥子人,都是他們隊上的同事,說趁隊長出差在上海未回來,便去夫子廟邊的天香閣,去捧歌女找樂子去了。」
丁氏聽了一臉不屑的說:
「又抽筋去了。這麼大把年紀還搞這一套,真氣人,小劉!我教你去叫糊紙匠來,你叫了沒有?」
「叫過了,明天早上來動工,三間房子五百塊,一天就可以全部完工。」
「好吧。」丁氏指著對面的三間房子對小劉說:「你把新買來的銅床搬進去罷。你要把房子打掃乾淨,不可以馬馬虎虎的,這是屠隊長的新房。」
小劉聽了連說是是是,絲毫不敢怠慢。他立刻走到廚房叫來朱司務,幫忙把銅床搬進新屋,安置妥當,費了好一陣子的時間,把房子打掃得乾乾淨淨,窗明几淨。
太陽落下時,陳嫂已準備好晚餐,只見客廳的邊門一閃,丁維庸嘴裡啣著雪茄煙,哼著二簧調子,提著一包鹹鴨香腸洋酒之類,春風滿面的走進客廳,他看見丁氏咧嘴一笑,張開嘴打了個哈欠正要說話時,就聽丁氏搶先斥責說:
「哎唷!我的庸二爺,你怎麼回來這樣晚哪,你瘋到那兒去啦?」
「別提了。」丁維庸放下東西,拍拍身上的灰塵半笑著說:「我帶著小劉去太平路買床,把床買好了。才出店門迎頭看見趙二同。他死皮賴臉的,硬拖住我去夫子廟,到天香閣捧歌女姚四鳳的場。他說她今天清唱梅蘭芳的全本鳳還巢,我若不去的話,他們幾個人要拔我的鬍髭,你說要不要命?」
「你把家裡事忘記啦?你想佈置樹東的新房要緊,還是去捧歌女要緊,你說?」她聲色俱厲的指著他說:「真是貓兒不在家,老鼠翻筋斗,你有沒有告訴趙二同說小玫已經到家了。」
「對他說啦。他說回到隊上就發電報到上海給屠樹東,我算他再兩三天一定回來。我要趙二同在電報中帶上一句,託他回來前把我們新訂的雲土催一下,他聽說小玫回來了,一定很高興!」
「小聲點。」丁氏一揚手說:「她在房裡睡覺呢。」
「你對她說清楚了嗎?」丁維庸睜著牛蛋眼說。
「說什麼?」
「屠樹東和她的事啊。」
「一一沒有。」丁氏像提不起勁似的說:「她昨夜到家已經很累,睡下後什麼話不說,一直唸著方明的病,聽她口氣頂多幾天她就要回到清江去。我去花牌樓拿來她的幾件新衣,說什麼她也不願穿,你看怎麼辦?」
「我看一」丁維庸又瞪著牛蛋眼說:「不如打開天窗說亮話,別顧前慮後的,話不說不明,燈不點不亮。」
丁氏聽了猶豫了片刻,她用手套在丁維庸的耳朵上說:「要她立刻改嫁給屠樹東很困難,欲速則不達,要慢慢的從長計議。」
「不行啊,屠樹東要娶她,十分猴急,不能拖,再拖必有變化!」
「我還是先要探探她的口氣,若把事情搞砸!對我們會大大的不利啊!」
「別多顧慮。」丁維庸把咬在嘴邊的雪茄屁股扔進痰盂,打了個乾嗆說:「只要是人,沒有不愛過好日子的,她跟方明那個窮小子苦頭吃夠了。你看她回來穿的那副窮酸樣子,知道她是多可憐哪?只要把話說清,我想她不會堅持的。你不說,讓我來!」
「你說?」丁氏臉色生氣。
「噯!我說。」丁維庸瞪著牛蛋眼。
「請你歇歇吧!我的庸二爺,你別一隻老鼠壞了一鍋湯嘍。你說她寒酸,她見了新衣就煩吧。」
「煩….?這可真奇怪了!」
「你知道小玫是知書通理的人,她又剛從中央地區回來,對於這裡的一切全都看不慣。尤其我們家是幹這一行的,雖然富有,她也不見得完全同意啊。再說一一」
丁氏要再說下時,陳嫂走來說:
「老太太,晚飯都準備好了,請你們來吃吧。」
丁氏點點頭,轉向丁維庸說:「吃完飯你還是出去,今晚你最好不回來,晚上我好好和她談談,希望她會同意,能有奇蹟出現。」
丁維庸聽他姐姐難得准許他不回來,趁機會出去找樂子,他心裡一高興就向丁氏笑著喊了一聲:
「喳!」他還咧嘴一笑說:「謝謝姐姐今天夜裡放我一馬,讓我去找趙二同他們,好好地到夫子廟一帶茶樓玩個痛快!」
丁氏見丁維庸一副老不正經的樣子,冷著臉說:
「年紀一大把了,不要樂極生悲,小心老命要緊。」
「你就別杞人憂天。我丁維庸是風月老手,我會見機行事,自有分寸。好了我先走啦。」
他說完中口還哼唱著不三不四的小調,向丁氏擺擺手咧嘴一笑,他正要走時,丁氏要他吃了晚飯再走。他說:
「小玫快睡醒了,你總要跟她打個照面哪。」
「好了。」丁維庸打了哈欠說:「我到我的房間小睡片刻,補足精神,吃飯再叫我。」
丁維庸伸個懶腰,回房小睡去了。丁氏隨即走進西廂房,扭亮電燈見黃玫側著身子睡在床上。
「玫兒!玫兒!」丁氏小心翼翼。
「什麼事嘛?」黃玫翻過身子,揉揉眼,不耐煩的問:「媽,你有什麼事嗎?」
「醒醒吧,吃晚飯啦。」丁氏慈祥的說。
「你們吃吧,我不要吃,我不餓。」
「不餓?不餓也要多少吃點嘛,媽站在這兒等你呢?」
「小玫!我們家的玫姑娘一」站在客廳的丁維庸,張著沙啞喉嚨,朝著西廂房高聲喊道:
「大家都在等你吃飯呢,菜都涼啦!」
「快一快起來吧。」丁氏拉住黃玫的手說:「你聽聽,你舅舅在外面等著你吃飯呢。陳嫂!你快打個熱手巾把,送來給小姐擦擦臉,聽到沒有?」
「哦!聽到了。」陳嫂趕忙端進一盆溫水,擰個手巾送過去說:
「小姐!請你擦把臉。」
黃玫皺著眉苦著臉,無可奈何從床上坐起來,擦了擦手就下了床。在大穿衣鏡前掠了下頭髮,就緩緩地跟隨丁氏走出房門。只見她舅父丁維庸笑臉迎人,直嚷著要請她上座。
晚飯時,氣氛很不調和,黃玫臉色凝重,對滿棹的佳肴一點胃口都沒有,丁氏也心事重重。只有丁維庸胃口特佳,他擰開一瓶日本太陽牌葡萄酒,吃著下酒菜,開懷暢飲,大吃大喝。他邊啃雞腿,邊掏出趙二同送給他的幾張戲票笑著說:
「姐姐!昨天從華北新來的日本精神藝術特技團,今天晚上七點開始,在新街口大華大戲院表演,聽說節目相當精彩,不同凡響。你和小玫去看看吧?也可以欣賞欣賞他們的東洋玩藝嘛,好不好?」
丁氏聽了笑著問:
「玫兒!你舅舅問你要不要去,看看日本東洋戲?」
「不。」黃玫臉色冷若冰霜說:「我還累得很,我只要好好安靜得睡一夜覺,那裡也不去。」
「維庸!」丁氏向丁維庸丟個眼色說:「她既然不願意去,就讓她安靜得在家睡一覺吧。我們娘兒兩人還要在家說說話呢!」
「也好。」丁維庸喝得醉醺醺,咧開嘴笑笑說:「我知道她旅途勞頓需要休息,我就不勉強了。那麼這樣吧,我要去找趙二同他們逛夫子廟一帶去找樂子,過了十二點,你就叫小劉槓上大門,你和小玫就好好談談。」丁維庸說談談二字,兩隻牛蛋眼向丁氏一瞧。
「你就走你的吧,鬼樣子!」
丁維庸臨走時,打個哈欠伸個懶腰,嘴裡不覺哼唱出「孤王酒醉桃花宮」的京戲詞,一扭一歪的走出大門。真的找趙二同一班子人,到夫子廟一帶風月場所,去尋找刺激。
子夜時,黃家又逐漸寧靜。
巷子裡每晚響起賣元宵的竹梆聲,和賣餛飩的小銅鑼聲,清脆聲中夾著鬱悶,讓黃玫難以入睡。
她無時無刻不惦念著她受了傷的丈夫方明,躺在醫院裡,日夜盼望地等著她回去,可是她又捨不得離開慈母,於是矛盾、不安的心情,在她的心頭起伏。雖然她寫了兩封信給方明提到頂多一週後就可以回到他的身邊,可是她害怕難以如願。她一想到這裡不由轉身向丁氏說:
「媽!」黃玫語氣果斷的說:「我想明後天就回去。」
「回去?」丁氏驚異地從床上坐起,全神貫注的問:「回到那裡去?」
「媽!」黃玫也不由地從床上坐起來說:「我不是對你說了嗎?方明他不是生病,是受了子彈的槍傷。現在還躺在清江的醫院治療。所以,我向媽要點錢,快些回去治好他的傷。媽!你能給我些錢嗎?」
丁氏聽了黃玫的話,沈思一會說:
「小玫!怎麼你才回來又要走?你捨得丟下媽媽?你爸去世得早,這十幾年來,我是吃盡了苦,受盡了罪,才把你養大成人。你竟忍心拋下我不顧,好不容易把你盼望到家又要走了。好吧,你要走就走罷,別管媽的事了。媽年紀老了,還能活幾年?想起來做人真沒有意思,鳴….鳴….鳴….。」
丁氏說著說著竟伏在鴨絨被上,嚎啕大哭起來了….。
「媽!」黃玫雙手摸著丁氏的背,一時不知說什麼好。
丁氏抬起頭一面哭,一面說:
「你不知道媽自你走後,幾乎每天都在求神拜佛,保佑你在外不要有三長兩短。總算黃家祖上有德,你平安無事回來,家運也愈來愈好。但是你舅舅又不能和我一條心,我不知被他瞞騙過多少錢?我像是啞巴吃黃連有口難言哪!好孩子你想想,我在世上還能活幾年?我是為誰辛苦為誰忙啊!你說你說?你要說話嘛?嗚嗚嗚….。」
「….」黃玫感到茫然,不知要說什麼話才好。
「我知道你現在長大了,翅膀硬了是不是?」
「媽!你怎麼講這種話!我!」
「本來嘛。常言說得好,丈夫是個隱壁牆,有了丈夫忘了娘!」
「哦!媽!」黃玫伏在一隻龍鳳繡花枕上啜泣了….。
「你也不必這樣,像這樣哭,媽想念你,我也不知哭過多少次了。好不容易把你盼望回來,你又要走了,唉!無怪說世道人心變得一天不如一天啦?連自己的親生女兒也是這樣啊?天哪!我真命苦哇!嗚嗚嗚….」
「媽!你!」黃玫不知要說什麼才好。她一股悶氣無法發洩,竟也鳴鳴嚎嚎的哭起來了。
丁氏聽女兒哭了,她心裡一驚停止了哭聲,怔了一會她嘆了一口氣說:
「怎麼,你也哭個不停,還要媽向你賠禮麼?」
「媽!」黃玫止住啜泣,抬起頭向丁氏說:「你為什麼老是用這些話來逼我?我真受不了,你知道嗎?」
「乖孩子!」丁氏口氣轉溫和說:「千說,萬說,你總是媽身上的肉,我怎能忍心逼你?只要你讓媽過得去,我就別無所求了。」
「媽!你有什麼過不去的事?」
「唔。你慢慢就會明白了。」
「不,現在就告訴我。」
「告訴你什麼?」
「你說過不去的事啊?」
「這個!我是為您著想。」丁氏見風轉舵說。
「為我著想?」她感到不解說:「這是什麼意思?」
「你不是擔心方明的傷勢嗎?」
「是啊。」黃玫覺得奇怪。
「那你可必急著離開呢?我打算!」
「媽!你打算怎樣?」
「一一」丁氏神祕一笑,未即答話。
「媽!你知道嗎?」我離開醫院時,答應他在半個月之內就回去的,現在已經有十多天了。而且他的傷需人照料,所以我想明後天一」
丁氏聽了雙眉緊鎖,怔了一會她說:
「過兩天,過兩天我要派人到清江去,把方明接到南京來休養一段日子,你看怎樣?」
「媽!你這話是真的?」黃玫感到驚喜不已。
「媽幾時騙過妳?傻孩子。」
黃玫不禁泛起一陣欣喜。
第二天清晨,丁氏趁女兒尚在睡,她輕手躡腳地滑下了床,她思前顧後地想如何才能撮合女兒與屠樹東之間的事。這時丁維庸像幽靈似的從外走進飯廳。
陳嫂看他進來,脫口叫他一聲。
「庸爺早!」
「不早了。」丁維庸向陳媽問:
「太太起來沒有?」
「起來了,在房裡洗臉呢。」
丁氏聽到丁維庸的聲音,從房裡走出來問:
「回來啦?」
「唔!」丁維庸乾咳一聲,未答話。
「昨天夜裡,你到那裡鬼混?」
「別提了。」丁維庸用手掌朝自己腦門一拍說:「看見趙二同那小子,硬拖我到姚四鳳家裡,又吃又喝又唱的。真他媽的折騰了一夜,現在還沒闔眼呢。怎麼樣,你對小玫說清楚了沒有?」
丁氏聽了緊縐雙眉,低聲的說:
「事情麻煩啦!」
「什麼麻煩?」丁維庸睜大牛蛋眼問。
「昨夜她對我哭了,還是惦念著方明,你說糟不糟?」丁維庸聽了,急得牛蛋眼睜得更大說:
「你就打開天窗說亮話,對她講明白要她別戀著那個窮小子,嫁給有錢有勢的,不就一舉數得嗎?」
丁氏聽了嘴唇一撇,搖頭擺手的說:
「我還沒說她都要回去,要是說了更要立刻走啦。」
「走到那兒去?」丁維庸急得眼像在冒火。
「她已經明白的對我說了,方明受的是槍傷!」
「槍傷!」丁維庸變了臉色說:「那一定是跟日本兵作戰的!不然的話,他怎麼會受槍傷?」
丁氏看著丁維庸,冷著臉向他說:
「怎麼樣,你想對他打什麼壞主意嗎?你可不能輕舉妄動哦,你要顧慮到小玫。」
「哎唷!這個我知道,不過….」
「不過什麼?」丁氏半笑半氣的說:「方明的槍傷一天兩天不會好的,所以小玫急著要回去清江仁慈醫院照顧他啊。」
「你答應她回去了嗎?」
「不。我答應她把方明接到南京來養傷。」
丁維庸聽了兩隻牛蛋眼一瞪,厲聲地說:
「這樣做怎麼可以呢。」
「你有沒有想到這件事的嚴重性呢?」丁維庸反駁一句。
丁氏聽了冷著臉說:
「哦!你當我真要把方明接來南京啊!這不過是緩兵之計呀!」
「緩兵計?」丁維庸有些不解。
「唔一」丁氏笑著說:「你想,我若不答應她把他接來,小玫她能安心的在家待下去嗎?」
「妙哇!」丁維庸兩手一拍,笑著說:
「姐姐!我真服了你啦。那你下一步棋怎麼走?」
「你一會先找個人,把他帶到我們家,當著小玫的面要他到清江把方明接來南京,實際上他不必去,只是穩住小玫的心。拖延至屠樹東回來,不就可以從長計議了嗎?」
丁維庸聽了丁氏這番話,不禁豎起大姆指向丁氏連聲說好。只見他鬼鬼祟祟向丁氏說:
「姐姐,你知道嗎?昨天夜裡趙二同告訴我,屠樹東已經打過電話。說他辦的那件大案子,已經掌握到寶貴可靠的資料,他一回來就可以配合日方的力量,把潛伏在南京的渝方特務份子一網打盡。對了,趙二同還給我些錢,叫我多找幾個心狠手辣的打手。」
「哎唷!我的庸二爺。」丁氏的聲音似在哀求:
「你要積積德,別幹這些傷天害理的壞事好不好?」
「我是受人之託,忠人之事。姐姐,請你別煩我,我要去找人啦。」丁維庸說完這話興沖沖的離去。
丁氏一把拉住他的衣襟說:
「哎唷!別忙別忙。你先把我剛提的人找好,話要說清楚。我們是要他來做做樣子給小玫看的。不是真叫他去清江接方明的,千萬別弄假成真哪?」
「這個我知道。」
丁維庸說完後,就轉身出門去找那人,一面去尋找流氓。可是,丁維庸對他姐姐說的話,黃玫聽得一清二楚。她想到潛伏在南京重慶的地下愛國工作者的生命,已經面臨危險關頭,她焦急如焚,忖思不知如何營救他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