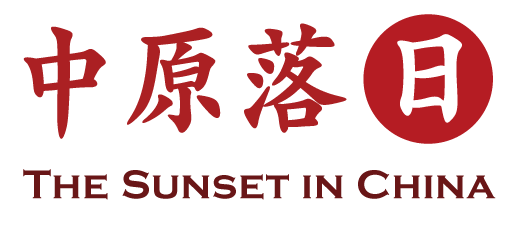
第三章
日軍佔領南京後,第一件事就是瘋狂屠殺善良難民。他們以清涼山的難民營為目標,將無辜的難民用武裝卡車運到下關揚子江邊,機槍掃射,這種瘋狂的大屠殺一連延續十多天。據留在南京的西方傳教士目擊,被殺害的人數保守估計超過三十萬人以上,令中華民族刻骨銘心。所以日軍盤踞南京後,這座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六朝勝地,竟成為魔鬼的世界。
於是殺戮、姦淫、搶奪、虐待、煙毒,形形色色,不勝枚舉,好人幾乎絕跡。都是那些不三不四的地痞流氓,而竟能搖身一變成為富翁和新貴了。黃玫的舅父丁維庸就是典型的例子。 自從日本皇軍進了城,他就千方百計的慫恿他的姊姊黃丁氏,做起鴉片的生意來。這樣不但可以投機發財,也可以滿足自己的癮頭。
丁維庸的姊姊,就是黃玫的母親,她在丁維庸花言巧語的誘說下,終於把畢生的積蓄拿出來,投資在這個本輕厚利的冒險生意上。由於經營日有起色,索興在大門前掛上榮記土膏行金字招牌。加上內外粉刷得煥然一新,每天生意興隆,顧客盈門,就連一般入時的新貴也常光臨。譬如說,日本南京特務機關所密探隊隊長屠樹東,就是黃家的常客。因他的鴉片生意,都是由屠樹東一手包辦進出貨事宜。由於獲得暴利,不到一年榮記土膏行,轉眼成為暴發戶。
這時榮記土膏行,因一時的光景興隆,男女僕役共有十多人,人丁興旺,錦衣玉食的生活。黃丁氏笑顏逐開,丁維庸也不愁吃穿了!」
這天是黃玫的母親黃丁氏的生日,屠樹東為表示慶賀,邀請一些朋友到黃家吃壽酒。晚間在黃家東廂房大吊燈奪目的光芒下,屋內空氣夾雜著濃厚的鴉片煙味,又傳來打牌聲、歡笑聲,此起彼落,熱鬧非凡。
這時,丁維庸正陪著屠樹東在東廂房吞雲吐霧,他燒好了一隻大煙泡安在煙槍頭上,恭敬地送到屠樹東嘴邊,樹東便對煙燈火苗大口的吸完煙,又呷了一口茶,吐出白色的煙霧,屠樹東便貪婪地笑瞇瞇指著牆上掛的那張大相片說:
「維庸一你憑良心說,你們一家子若沒有她一我….哈哈哈哈….」
「是是,東爺,你說得不錯,我這個外甥女過去是學校有名的校花啊。人是挺聰明的,就是脾氣有點….只要東爺你不嫌….」丁維庸接著也是一陣狂笑。
「說正經的;維庸。」屠樹東半帶著怒氣說:「這可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啦,自從一年前我到你家看到這張照片,黃伯母和你就一口答應要介紹你的外甥女,說她在鎮江姨媽家,很快就會回來。所以,這一年多來,我極力配合你們,說話從不打折扣,可是你們都在騙我,說她就快來了。然而,現在卻連個影子都沒有,你說,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?告訴你,你再騙我,可別怪我!」屠樹東咬牙切齒地說,從腰裡拔出一支手槍晃了一下….
「東爺!」丁維庸心裡一驚,放下煙槍笑著說:「別急嘛,我丁維庸敢對天發誓,如果這些天再看不到她,我便任由你處置,好不好?」
「有把握嗎?」
「當然囉。」
「你再騙我,當心你的腦袋哦!」
丁維庸正一籌莫展,黃丁氏忽然進房門笑著說:
「樹東!」她的聲音沙啞:「怎麼,你又在犯老毛病啦?是不是心情不好啊?」
「哦!伯母。」屠樹東挺身坐起,笑得有些勉強。
「對!我姐姐來了,我不說啦,你問她就知道我的話是不是真的。」丁維庸說完,又躺下燒他的大煙泡。
「是怎麼一回事啊?樹東?」黃丁氏半氣半笑地問。
「嘻!」屠樹東收起左輪槍笑著說:「沒事沒事。我剛才問維庸,想知道黃玫姑娘幾時回來?」
「哦!這個呀?」黃丁氏露出神秘又驕傲的神情:「像你這樣猴急,也許讓你等上個一年半載也說不定唷。」
屠樹東聽出黃丁氏像是話中有話。便露出一副奸詐的神情說:「我若是不猴急呢?」
「你若是不猴急嘛!唔,也許她在兩三天內便回來。」
「真的?」屠樹東歡喜的從床上翻起身來,笑著問:
「伯母!你此話當真?你沒騙我吧?」
「有信為證。」
「有信?」屠樹東兩眼睜大的問。
「哦!」黃丁氏感到有些失言。
「信上怎麼說的呢?」屠樹東逼問。
「這….」黃丁氏話語有些猶豫:「你不相信我的話嗎?」
「我!我怎麼敢不相信,我一」
「啊唷一」黃丁氏雙眉深鎖:「你就別打破沙鍋問到底,老實告訴你,那是帶來的口信。」
「口信?」屠樹東感到有些迷茫。
「東爺!」丁維庸趕快解釋說:「我丁維庸擔保三天內她一定回家,別嚕囌了。躺下來抽吧。」
那桿象牙質的大煙槍被丁維庸裝上一個圓型煙泡,恭恭敬敬的送到屠樹東嘴邊,他便呼呼抽起來,黃丁氏見狀趁隙溜出房門去照料其他煙客去了。
丁氏離開房間一會後,只聽鐘噹噹的敲了十一下,時間已十一點。忽然大門外傳來一陣汽車喇叭聲!
「咦!怎麼今天汽車會來得這麼早?」丁維庸邊燒大煙,邊咕嚕著。
屠樹東吞下一口煙,呷了一口茶,半睜鼠眼說:「不是吧?怎麼喇叭聲不對?」
屠樹東的話音才停,屠樹東的助手趙二同進門就喊:
「隊長!」趙二同一聲立正,又行個舉手禮。
「什麼事啊,二同?」屠樹東躺在床上垂著眼皮問。
「谷村聯絡官,請隊長馬上回去。」
「什麼事啊,這樣急?」
「他要你搭今夜十二時零五分夜快車到上海。」
「到上海?」丁維庸聽了有些詫異。
屠樹東雙眉緊縐,向趙二同問道:
「你知道是什麼事嗎?」
「詳情我不知道,我看山佐顧問和谷村連絡官,交頭接耳談得很機密。」
「談什麼?」
「都是日語,我全聽不懂。」
「把你聽懂的說來聽聽吧。」
「大概是因為上海破獲了一件案子,這案子是與渝方潛伏在南京的特務份子有關。」
「哦!有這樣的事?」屠樹東睜開鼠眼,顯出驚異的神色。
趙二同走前兩步,接著說:
「所以,聯絡官很急,請你快回去。」
「好吧。你先走,說我馬上就到。」
「谷村連絡官因隊長車子臨時出了毛病,便和我一同來接你,我看還是一起走吧,還要到下關呢,別誤了火車的時間。」
「也好。」
屠樹東從容地下了床 。丁氏已從房外走進笑著問:
「怎麼又有事了嗎?樹東?」
「是的。」他拿開雪茄說:「不但有事,還是一件挺麻煩的事呢!」
「什麼麻煩事?」
「到上海。」丁維庸湊上一句。
「是的。」屠樹東嘴裡應著,貪婪的眼神斜視牆壁上黃玫的那張大相片。
「幾天能回來?」丁氏凝神問。
「說不定。」屠樹東吹吹煙灰說:「我想不會超過一星期吧。」
丁維庸向丁氏使了個眼色。
黃丁氏看了心裡會意,她笑著說:
「樹東!你別心急,我想你從上海回來,一定能看見我女兒黃玫。」
屠樹東聽了不禁心花怒放,取下雪茄仰臉哈哈大笑….。
他得意得靈機一動說:
「伯母一我最喜歡聽你說句話。」
「不過,你也要打算打算。」
「打算什麼?」
「初次見面,不帶點見回禮嗎?」
「這當然。」屠樹東又仰臉哈哈一笑。
「姐姐一」丁維庸忙對丁氏說:「怎麼我們上次訂的貨還未到?我想請東爺到上海順便問總行,如果已經出發了,想請東爺代我們再訂一批,最好還是雲土。」
「樹東,你聽見沒有?」丁氏笑著說:「省得我再說第二遍了,就照著維庸的話拜託你嘍。」
「遵命一」屠樹東把遵命二字,說得像唱戲對白那樣地有韻味,聽得丁氏和丁維庸眉開眼笑。
一直站在旁邊等候的趙二同,臉色有些不耐煩說:
「現在已經十一點一刻了,快點走吧,谷村連絡官和山佐顧問都在等隊長呢,別誤了到上海的火車時間哪。」
「好。」屠樹東笑著向丁氏一揚手說:「伯母,等我上海回來見。」
「你就安心去吧,早去早回。」丁氏滿面春風說。
「只見屠樹東提著他的黑色手杖,跨步走出了房門。他突然回頭向丁維庸說:
「維庸!我也有一件事拜託你哦。」
「東爺,你請說,只要我丁維庸能辦到的,我一定辦。」
「如果我仍在上海,而玫姑娘已經到家了。你叫趙二同打個電報給我,可以嗎?」
「這一定,一定。」丁維庸鞠躬唯唯示諾。
於是,見趙二同帶著兩個爪牙,簇擁著屠樹東走出了黃家的大門,隨即上了汽車。一溜煙地開出黃家的巷道。
屠樹東走後,其他的煙客也陸續回去。這時黃家東廂房牆上的自鳴鐘,指針正是十二點。巷內不時傳來賣元宵的竹梆聲,有時還夾著賣夜餛飩的小銅鑼聲。在仲夏之夜,使得這座歷史悠久的江南名都,別有一番鄉土風味。
丁維庸在屠樹東回去後,他才能躺在床上抽鴉片抽個痛快。一口連著一口的抽,頓時忘記自己身處何地。
黃丁氏雖然未上煙癮,怎奈整日的忙碌,精神相當疲倦,也想弄兩口大煙解除疲勞。丁維庸了解他姐姐的習性。他就把燒好的一口煙遞給她,黃丁氏也躺在床上煙燈旁邊,把槍頭含進嘴,但由於不擅此道,便打了兩個咳嗆,她吸完後喝口茶,又長吁一聲吐出煙霧,表現出愉快的樣子。
這時,佣人陳嫂端來冰糖蓮子湯和人參桂圓湯。
「姐姐!」丁維庸吃了一口蓮子忙說:「屠樹東這小子,真有點不好纏哪。雖然我們的生意多虧他幫的忙,我總對這小子存有三分戒心!」
「這也難怪。」丁氏說:「記得我們去年生意才上軌道,他第一次到我們家裡,對牆上小玫的照片一時著迷,願意幫我們的忙。憑良心說,這一年來我們那次不是在騙他?若不是最近真的接到小玫的信,剛才那些話我才不敢說呢。」
「有什麼不敢?」丁維庸連忙坐起,捲起衣袖像是動了肝火似的說:「就憑他對我拿槍動刀的,哼!他媽的,這年頭一」丁維庸說到這裡,氣狠狠地想再說。
「別再說了。」丁氏手一揮:「你別在閑地罵皇帝了,小心禍從口出。說實話,他也真的幫我們家大忙。」
「你說屠樹東是皇帝?呸!他不過是日本人手下的一條狼狗,是善良的中國人眼中的屠夫,姐姐我的話對吧?」
「好了。小心隔牆有耳。小玫信上說,方明的病很重,身邊的錢早已用完了。小玫!我這可憐的孩子,這一年多來,不知跟那個窮子小受了多少罪啦?」丁氏一面說,一面嘆息….。
丁維庸聽了睜著牛蛋眼說:
「姐姐!你也不必擔心,我想小玫最近兩三天就會回家。」
「看她來信日期就知道了。」
「信呢?」丁維庸噴出一口煙霧問。
「哎唷!」丁氏拍了下大腿說:「還被我放在抽屜裡呢。」
「啊呀!」丁維庸把煙槍向煙盤裡一丟說:「真危險哪,若被屠樹東看見信上方明的名字,那麻煩就大啦!」
丁氏聽維庸這樣一說,心裡頗為不安,立刻取出女兒的來信。她看了遞給丁維庸說:
「你想我們收到信也快十天了,小玫還沒回來。」
「姐姐,你別急,依我盤算她早已離開清江,正在回家的路上,很快就會到家的。」
「維庸!」丁氏皺著雙眉說:「現在我倒有些心神不安起來了!」
「為什麼?」丁維庸突然睜開兩眼問。
「我怕方明會和她一起回來。」
「不會吧。」丁維庸神情一怔。
「這怎麼能說得準呢?」
「我想一第一,」丁維庸乾咳一聲說:「第一,是你只要小玫回來,並未提及方明;第二,方明的病不會好得這麼快;第三,聽說日本軍最近在江北一帶開了一次大火清鄉,中央隊伍損失慘重,傷亡很重。方明是在中央軍裡做事,應該已經受傷。既然受傷,怎麼回得來呢?姐姐你就別擔心啦。」
「不過!也得防備防備啊。」
「我想一」丁維庸,抽了幾口閉著眼吐出煙霧,呷了一口茶,冷笑一聲說:「我想方明不來倒好,他若是真的跟小玫同來的話….」
「怎麼,你想幹嘛?」丁氏盯著丁維庸臉問。
「那一」丁維庸臉色陰沉地說:「只有一條路。」
「什麼路?」
丁維庸悶笑一聲,未說話。
「說嘛,鬼樣子!」
丁維庸坐起來,兩眼一斜,斜著腦袋說:
「他既在中央軍做事,不是名符其實的抗日份子嗎?」
「你想怎麼樣?」丁氏表情有些緊張問。
「咯嚓!只要去檢舉,他必被砍頭!」丁維庸丟下煙槍,兩手還比個殺頭狀。
「一一」丁氏搖了搖頭,輕輕喃著說:「你這樣做未免太殘忍又缺德。況且,還要顧慮到小玫。」
「有什麼好顧慮的,你就別婆婆媽媽的吧。」
「你是知道的,她和方明訂婚之後,因避戰亂讓兩人感情更好。」
「這樣做,才能斬草除根,不留後患哪。」
「一一」丁氏又搖頭,半晌才說:「你這樣做我不同意,做人不能太絕,再說我們還受過他的好處。」
丁維庸聽到這裡,把手中煙槍丟向盤裡,生氣地說:「你受過他的好處,我丁維庸可沒受過他半點好處啊?想起從前的事,真氣得老子牙癢癢,恨不得….」
「我想方明他是一個正直的人,他怎麼跟你結下樑子呢?我真不懂,你別冤枉好人哪?」
「他是好人?呸!好人還見死不救?」
「救你什麼?」丁氏感到不解。
「就在前年初,我的癮頭犯了,向他借十塊錢買煙過癮,他不但沒借給我,反而對我說,抽大煙的人該殺頭!真他媽的,想起來真恨死他了。」
「好啦。」丁氏擺擺手說:「過去的事別提啦,要替小玫想想吧。」
「小玫有什麼問題?」
「我擔心她不會看上屠樹東的。何況她與方明有婚約在先,我愈想問題就愈難解決。」
「啊唷!我的老姐姐,」丁維庸嘴邊噴出涎沫說:「你呀!你不懂現在的女孩子。別說!就是孫猴子豬八戒,只要他有錢,就是最優秀的女人,最美麗的女人,也會崇拜他的。小玫也是女人哪,她怎麼能逃得過?」
「你這樣說,也未免把女人看貶了。」
「我是實話實說嘛。」丁維庸說完,得意地笑….。
「鬼樣子!」丁氏沉著臉色說:「若是小玫硬是不願與屠樹東在一起,你說怎麼辦?我擔憂的是這點。」
「這點你放心。」丁維庸晃了晃腦袋笑著說:「只要照著我的話開導她,一切搞定。」
「怎麼講?你有什麼錦囊妙計?」
「錢哪!」丁維庸笑著說:「還有地位啊,老實說屠樹東今天在南京有錢有勢,除了日本人誰能比得上他?你想小玫難道要跟方明窮苦一生。」
丁氏仔細聽了丁維庸的話,躊躇了一會拉長臉說:
「不論怎麼講,他們總是有婚約啊。」
「婚約有什麼屁用,時機不一樣了,哎唷!我的姐姐,你真是愈老愈糊塗啦。」
「可是,也不能操之過急啊。」
「依你之見呢?」丁維庸瞪著兩隻牛蛋眼問。
「還是隨機應變吧。」
「別弄巧成拙啊!」
「我看只有見機行事囉。」
丁維庸一面和他姐姐說話,一面又呼呼地抽起煙來了。
牆上的自鳴鐘敲過深夜一點,黃家的僕人們把各人的事情做完後,不一會工夫,院內恢復一片寂靜。
